
读《王耀东诗文选》使我进一步想到美国《新大陆》诗刊在2001年发表的诗评家刘耀中的一篇关于“美国诗人罗拔·弗罗斯特”中的一段话,他说:“在中国诗坛上,我特别关注王耀东的新乡土诗,他探求了一条诗神之路,他的诗已经不是习惯意义上的乡土诗,如变形、隐喻、象征、幻化、畸联等,是诗歌观念和审美超向的根本变化,这种精神变化和弗罗斯特是相通的。”这一段话实际是指出了大陆乡土诗人王耀东和美国19世纪桂冠诗人产生了历史性的对接。大家都知道,诗人与作品历来是见仁见智,各有所好,那么大陆上王耀东的诗怎么就和美国诗人扯到了一起呢?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在发行《王耀东诗文集》的时刻,让我见到了这位诗人,并同这位乡土诗大家进行了访谈。

果然,文如其人,同王耀东的这次交谈,如读他的诗,他人朴素而且使人愉快,简练而且深情。我问他:“你喜欢美国的乡土诗人弗罗斯特吗?”
答:任何诗人都有过自己在岁月中的挣扎,美国这位诗人,经历也很艰难,但他很刻苦。少年时期,在农场劳动过,还当过织布工人,很能吃苦耐劳,他写诗是受母亲的影响,虽然他写诗,但没有写出名堂,快四十岁了,去了英国,接触了英国“乔治安派诗人”,从此一举成名。我是在八十代,在一本外国诗集上,读过他的诗。我赞成他对诗的观点:即“文学是净化生活的,它能去掉社会上的一些杂质。”是的,我们的灵魂依附于这个世界,诗人在不同的区域塑造了各自的灵魂,我们还要把她归还给这个世界,这些就是诗人的归宿。

问:弗氏有一首著名的诗篇叫:没有走过的路,诗中说,人生有两条路,一条是寻常人走的路,一条是无人走过的路。你走过的是哪一条重要的路呢?
答:弗罗斯特一生喜欢探索,重视自己的感觉,他死后,从他家里发现了一千多封没有发出去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思维活动,那就是倾诉自己,这种对诗的探求与倾诉他不想让人知道,实际是述说了诗人艰难探求的悲伤史,重视灵魂深处的这种开掘,就是一种不同的诗人之路,敢于向灵魂深层倾诉,找到自己的制高点,是不容易的事。我开始写诗注重事件的描写,往往不注重开掘心灵的细节,结果把那些土的掉渣的又值得捕捉的细节忽略了,后来明白了,我们忽略的往往也是最值得诗人去挖掘的。例如乡间那些不起眼的事,在农人看起来都是极平常的事,然而你换一个诗的角度,用诗的眼光去观察,就感到新奇了。在80年代我写过一首“他要挺起的”诗,写的是一位农人进自己新盖的房门时,不经意的弯了一下腰,这个“弯腰”和“一个挺起”是一种历史的巨大变化,想“挺起的”是一种自信,结果被贫穷压弯了,是很难再挺起来的。此诗引起了当时诗坛的广泛关注,出现了不少评论。咱们有一句话,叫老树开新花,是极平常的事,也是习见习闻的事,如果用诗去挖掘它的新花,就有了新趣,新奇。写乡土没有“土”怎么行呢?有土才能生新芽。我从小就是趴在地上,吃土抓土,是身上沾满了泥巴长大的,我那时一闻到土就觉得很香,在干活时鞋中都塞满了土,汗珠和土搅在一起,没有觉得鞋里臭啊!这些看起来非常朴实的甚至还有点愚昧的、苦涩的、丑陋的细节,往往是发现神奇故事的精神支点,所谓乡土性最重要的是要从农人的伤痕中发现心灵的苏醒。我从小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十四岁就学习用木轮车推煤,挑水,在河滩挖沙种瓜,这些受苦受累的活儿,现在看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没有遭难的感知,也写不出有自己乡土感悟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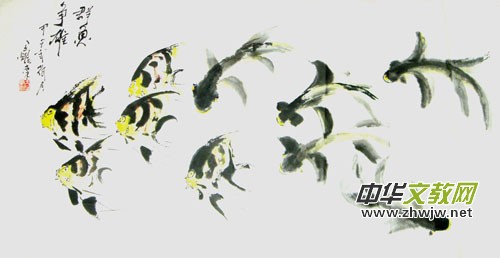
问:你的述说,让我很感动,你这一生也非常不平凡,能执著追求自己的乡土诗,不像有些写乡土诗者,就刮一阵风。
答:我读弗罗斯特的诗,思想上经常产生共鸣,就是那种真实感。乡土最重要的在于朴中有真,弗氏喜欢大自然,认为世界上只有经过原生的自然的洗礼,才纯朴、真诚、所以他特别喜欢大自然的空气,喜欢大自然的流水,其实这是他灵魂深处的奥妙。这也是他与同时代诗人的不同性。也是他成功之处,他是用乡村的哲学,农夫的眼光看待一切,于是他的诗就是他自己的世界。也就有了他的个性和特色。
问:这一点你俩有共同之点,我喜欢你写的“最初的歌”、“拔节之韵”、“扬麦场上”、和那些写母亲的诗,读起来就觉得是自己身边的事,动情处还让人流出泪来。
答:我有我的立足点,就是一个农民儿子对自我的审视,用一个农民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故土上的人、事、及风俗人情,其实就是诗的“能”,一种诗的磁场,这些东西都潜藏着诗的无尽的创造力,对于它神奇的发现,就是乡土自身的一种醒悟与感觉。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诗人告诉我们,神幻源于一种真实,这个真实却是原始的,它比人的情感更深沉、更难言、更便于流传,这就是艺术的胚胎,就是艺术的磁场,在我们的生活中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能量。抓住了它,就抓住了诗人创造个性与特色的核心。
问:人人都有自己的梦,我发现你的梦一直放在乡土上,七十多岁了还没有离开,这是为什么?
答:人的梦都在头顶上放着,就是说放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不管别人怎么放,有的人甚至是放在城市的高处望乡土,我与他们不同,我把梦始终放在了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上,这里有根有花有果,一代代长着麦穗的金黄,这里有一代代不会衰竭的梦幻,凝聚着乡土的灵魂,一代代发出神圣的呼唤。
问:时代变了,商业的欲望影响了人们对贫困乡村的看法,做为一个诗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问得好。这也是现代诗的一种苦恼,所谓现代,从根本上说,就是日益发展的高新科技和日益膨胀的贪欲粘在了一起,一切都表现在利欲上,市场利欲的驱动,把纯净的诗篇排挤到了最边缘的位置。写乡土唱乡土越来越变得不值钱,生存都困难了,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其实这种东西本身就不是一种商品价值,从本质上讲,文学的使命不是轻了而是重了,我们的诗我们的文学,要告诉人类的是:污染是对大自然的破环,乡土地上处处拆迁,是对原生态的破环,这样就赐予了诗与文学更深刻更伟大的使命,那就是呼唤乡土的阳光,食物和水,呼唤人的良知与美、善,来保护我们的地球和人类,诗如乡土地上的布谷鸟、净化剂。时代在发展,诗表现手法不能退化,也要不断的更新自己,自觉跟世界先进文化对接。要与时俱进,用诗与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述说。一部《红楼梦》,它是世代能传承的财富,唐诗宋词,有的甚至仅仅是几句话,却能让一个民族蓦然苏醒,就是这些不易说清的诗与文学,述说着乡土诗的灵魂情结与走向。并能产生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
问:还有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大家对你的乡土诗,前边加了一个新字,是新乡土诗!乡土诗和新乡土诗有什么区别呢?
答:这个问题很重要,一是说写新乡土诗,它的具有新的时代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创新,乡土诗实际是古代的田园诗的别称,乡土、田园应该说内涵是一致的。新乡土是不仅仅是一个叫法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乡土诗要有它新的诗意的深层结构,现在的田园已不再是陶渊明时的桃源状态,而是具有荒原化的现象,从农人心理结构上讲,现在乡下人有一种失落感,传统化的心态遭到叛逆,对乡村的前景出现了断裂意识,乡下人到了城里会不自觉的产生自我失调感,具有个性化的乡村从心灵上趋向了弱势化,另一种是诗的表现手法由于受西方文化的渗透,有一种杂交现象,多元文化的结合对乡土诗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示性。读现在的乡土诗和五十年代写的那些乡土诗觉得大不一样,乡土这个老字眼儿是在新条件下新异的陌生词。所以说,写新乡土诗一定要写出俗中的不俗,不凡中的不凡,不神奇中的神奇。思那已去者,盼那将至者,抓住新发现,发现新珍宝。
问:你既然谈到了时代的异化对新乡土诗的影响,那么做为一个乡土诗人如何面对这个现实,走出自己的道路呢?
答:世界著名诗人帕斯说过:“现实是遥远的,它是一个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抵达的东西。”帕斯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现实是指诗意的现实,并非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如何用诗去揭示乡土这个现实,是诗人必须着力追求的东西,如何表达了这种现实?这就是诗人面对的一种挑战,写乡土并非不现实,写乡土并非已遥远,时代精神对乡土的投射是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乡土如何与现实去对接,诗人的意象之源又在哪里?,所使用的心象、心绪、魔幻,都应该是乡土中的珍宝,是诗的神秘世界。时间是贫穷的,在诗确立诗的本质时,首先要确立它新的时间,这就是现实,诗看起来不是真实的,而本质却是最真实的,乡土诗要写好她的现实性,说到家是如何对自身的一种重新确立,是一项坚实的又是神圣的活动,不应该局限于象与不象之间,而应该是人类灵魂的一面镜子,
我们都有一颗脑袋一颗心,都有两只手、两只脚,谁能离开脚下这片土地呢?只要我们认准了净化的目标,左右开弓,双向进取,凡是阻挡我们前进道路的石块、坎坷,一定要排除、越过、要勇敢的冲过去,带着你的原生态和乡土给你的气息,敞开自己的心灵,这样就决定了你的情调与特征,这就是诗人高扬的态度与使命,我相信,只要钟情于此,献身于此,一条崭新的路会踏出来的。
(作者:绿色中国网总编 显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