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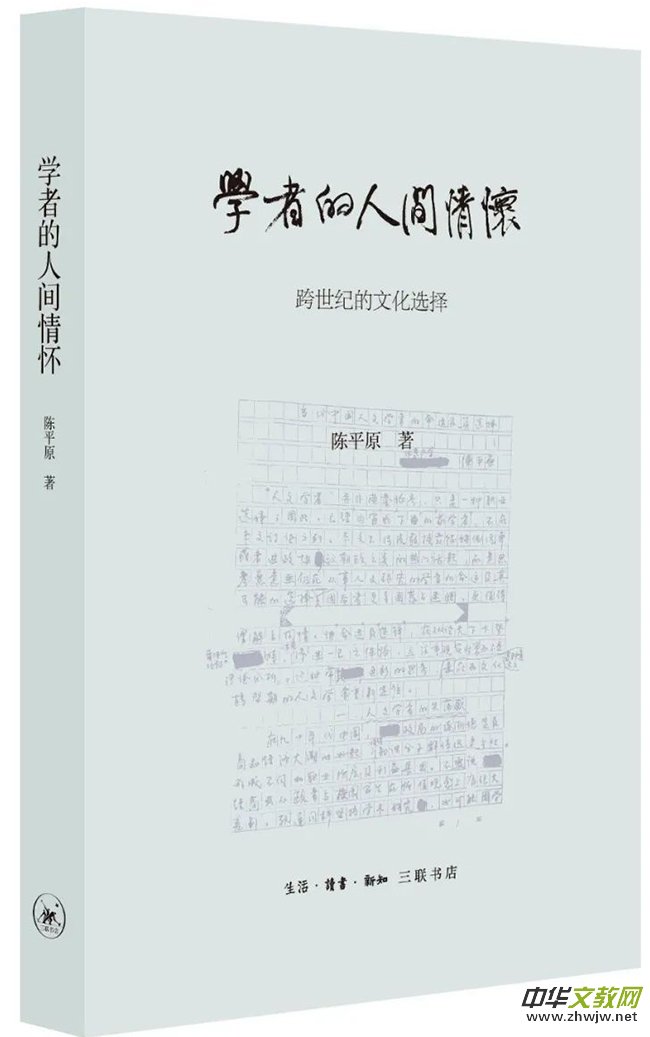
近年,中国教育体制及教育观念发生了大的变化,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与发达国家的教育状况不同,中国教育充满矛盾,也充满生机。这种状态,单从入学年限、课程设置以及就业途径等无法说清。理解这种教育转型过程中的痛苦及其可能性,必须以近百年中国文化进程为背景。
以教育为立国之本,中国人有此传统。晚清康梁提倡改革,以废八股兴学堂为突破口,这既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刺激,也符合中国古已有之的“学为政本”的观念——这里的“学”,包括文化教育与思想学术。可是,出于对落后挨打局面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国富民强、迅速崛起的殷切期待,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对“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革命更感兴趣,而相对忽略了“百年树人”。“教育救国”的口号,很快消失在炮火硝烟之中。从毛泽东的“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到邓小平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再到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总算逐渐走上正轨,但在我看来,问题仍然多多。如果说可能对下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卡脖子”的,我以为不是经济学家大声疾呼的能源匮乏或交通瘫痪,而是积重难返的教育危机。正因如此,在中国,教育不仅是教育家的事情,而是每个有良知有远见的知识者都必须关注的问题。我不是教育家,只能从一个普通知识者的立场,谈论几个外界感觉新奇的现象。
首先,如何理解近年中国出现的“学院”改“大学”热潮。许多国外朋友对此表示困惑,问我为什么要把“化工学院”改为“化工大学”,“师范学院”与“师范大学”到底有多少差别?这个问题应该由国家教委来回答。按教委规定,“大学”的办学规模、师资队伍以及课程设置等,都应不同于“学院”。在我看来,关键不在于这些可以量化的具体指标,而是体现了中国教育路线的改变:由师法苏联转向借鉴欧美。
晚清的学制设计者,喜欢说“上法三代,旁采泰西”。前者是门面话,后者才是实情。而“旁采泰西”又往往以日本为媒介,故其清末公布的各种教育章程,受日本影响很深。1902年发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明确区分“高等学堂”与“专门实业学堂”,第二年,又有《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八科,“京师大学务须全设”,外省大学可以酌情减少,“惟至少须置三科以符学制”。这种纸上谈兵后来有所修正,1914年《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鉴于各地经济实力及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主张“大学校单科制与综合制并行”,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单科大学总是不如综合大学正规。
50年代初(1951—1955),学习苏联,进行院系大调整,出现大批“单科大学”,并按其专业改称某某学院。“学院”之不同于“大学”,就在于抛弃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通才教育,而改为强调实用性,其中尤以文、理的分离最为突出。减少专业,强调实用,不只是使得学生知识面过于狭隘,而且由于国家重视“实业”而忽略文法财经(比如政法系科的学生,1947年占大学生总数的24%,1952年降为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及现代管理影响极大。另外,在单科制的学院里,文理渗透以及科际整合无法展开,难以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当然,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面对并接受西方文化有很大关系。在此意义上,我对“学院”改“大学”持欢迎态度。只可惜中国的事情总是一哄而上,如今的大学改制也有很大的盲目性。
其次,我想谈对近年大学“经商自救”的看法。从研究所办公司,到教授卖馅饼、北大拆南墙,新闻媒介做了不少渲染,以致成了在国外常被询问的话题。中国的大学教育长期靠政府拨款,专业设置以及研究课题,因而也就受制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教育体制的变革,大学的课程设置,开始受资金来源和学生择业的制约,这是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潮流。可要是说综合大学不搞科技开发,便容易知识老化,对最新学术发展不敏感等,这最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政府“没钱”办教育,而不得不将大学“部分地”推向市场。并非所有的学科都能靠“转变观念”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比如数学、文学、天体物理等。教育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的“长线投资”,不可能马上回收。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至于愚蠢到要求哲学家去搞“科技开发”;可研究经费的缺乏及教师薪水的微薄,使得许多大学校长以及各系主任都以“创收”为硬指标,而相对淡漠不能马上来钱的日常教学和基础研究。在没有基金会支持的情况下,将大学教育推向市场,在我看来,弊病极大。目前,整个中国教育界弥漫着商业气氛,即使短期内能救急,其后遗症也相当可怕。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再次,我想谈谈近年发展颇快的私立学校。“学在民间”,本是中国的传统。自孔子首开私门讲学与著述,两千年来,私学与官学并存。在某些特定时期,前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甚至比后者还大。晚清变法维新,康有为与章太炎在官学、私学之争问题上意见尖锐对立。前者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变革,“伏乞明降谕旨”,强令民间的书院、社学、学塾改为新式学堂。这种思路,隐含着由政府统制教育的要求。1949年以前,由于政府经济及管理能力有限,私学仍长期存在。194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中,私立者占38%(上海甚至达到75%)。中、小学(包括私塾)中,私学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50年代,随着教会学校的取消与各级私立学校的改为公办,政府对教育实行了有效的控制。这种一统化的教育体制,以及将学校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思路,虽有利于“思想改造”,但切断了民间办学的优良传统,使得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根本无法实现。由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教育观念的转变,政府开始调整策略,重新允许私人办学。
90年代中国教育的一大景观,便是私立学校的大量涌现。1993年初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境外资金独立创设综合大学的步子不会迈得太快,所谓“贵族学校”的提法也会受到某种限制。但总的来说,私学的恢复以及可能的发展,必将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教育体制的改变,短期内是“救急”,即调动民间的资金,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贡献。长远来看,对实现教育的相对独立,允许并鼓励多种声音、多种观念的并存,进而改变已有的中国文化格局,会有更加积极的影响。
最后,谈谈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把它留在最后讲,并非因其不太重要,而是这话题太沉重了,以致感觉颇难开口。前两天,有位日本朋友指着中国政府公布的1993年统计公报悄悄问我:这是真的吗?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那么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辍学?到过北京、上海、广州的外国朋友,大都不能想象中国还有近两亿文盲。单解释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有限,实在不得要领。十年改革,成绩有目共睹;唯独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不够,从长远看是一大失误。开展“希望工程”以及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办学,只能起缓解危机的作用。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太低,国内舆论始终不以为然。如果中央政府无法用立法程序来规定教育的投入,在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教育第一”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方面,国外的报道已经很多,我没有更新鲜的说法。再说,不曾从事实际的政治操作,不了解政府决策的内幕,只是意识到中国教育目前潜藏的危机,并对此表示深深的忧虑。至于政府的苦衷以及改变现状的良策妙方,只能请教国家教委,我没有权力越俎代庖。(1994年初春)
编辑:红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