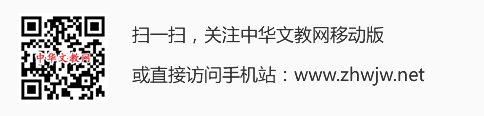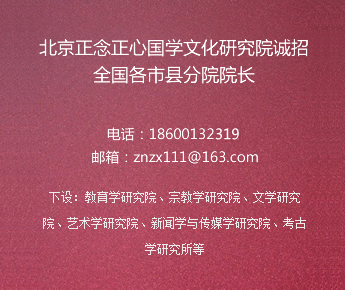每当感觉自己快要被生活的洪荒冲走的时候,我就会随便钻进一辆公交车,任凭它拖着我绕武汉三镇瞎转悠,仅仅只是为了找到自己在生活中存在的证据。公交,是一个城市最大众化、最底层的场所,五湖四海、三六九等都在这个小空间里聚了散、散了聚,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必认识谁。路旁的风景,无论好的景致还是坏的景致都疾速地从车窗外掠过去,这感觉如同人生的某种际遇一般。
从起点上车,也将会从起点下车,人生已无所谓起点和终点。等我上车时车厢内已座无虚席,我只得在拥挤的车厢内勉强地站着,眼巴巴地羡慕那些能安逸地坐着的人。我不能怨别人占尽了地理优势,只能怨自己来得太迟。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打扮靓丽的长发女郎,一身火辣的穿着丝毫不逊于武汉夏天火辣的天气。她左手紧紧地扶着栏杆,右手警惕地护着胸前的包,时而还得腾出一只手整理一下被车窗外呼啸而过的狂风“毁容”了的发型。坐在我最前面的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爷爷,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如同被揉皱后随意丢弃的白纸般,让人不忍直视。许是乏了,他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仿佛一段停下来了的时光,我还未来得及把车厢里的人看分明,车子就到了下一站。车上的乘客陆续下去,又陆续地上来,让人不由得生出了人生的变化无常之叹。
旁边的位子空了出来,我补了上去。上车的是一对母子,小孩约四、五岁的样子。一上车就叽叽喳喳地在车厢内蹦开了,把夏天的活力也一并带了进来。母亲一边刷卡一边叮嘱孩子不要乱跑。许是见了车厢内的陌生面孔充满了好奇,小孩仍自顾自的闹着,全然不顾母亲的叮嘱。那位母亲在我身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把孩子搂在怀里,小孩在母亲的怀里欢快地玩闹着,时而学着车内的广播声,时而冲着我顽皮地叫着“姐姐、姐姐”。我仿佛看到,我的童年在我的眼前笑开了花。而现在的我却在一个还没准备好长大的年龄就长大了,还没准备好适应这物欲横流的社会,童年就这样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我。
跟着上车的是一位腋下夹着公文包,一身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打扮得干练利落,一张世故的脸上已看不到丝毫的棱角,许是在生意场上久经历练的缘故吧,他几乎是溜进车厢的。生意人,无论在哪,似乎总能让自己左右逢源。他的眼神飘忽不定,一上车就四下里搜索着空位,那样子像找商机似的。他的眼神扫到了我的身上,我隐约感到了丝不安。
紧接着上车的是位衣着朴素的女人,拎着大包小包,嘴里喘着粗气。她眼神呆滞、眉头紧锁,一张腊黄的脸上写满了生活的苦楚和无奈。不难看出,那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喘不过气来的不幸女人。城市生活的压力,微博的收入以及子女的学业负担造就了这类女人的共同表情。我不仅难过起来,在我这个年龄的她,也曾是一位无忧无虑、怀揣梦想的天真少女吧,生活真是把“杀猪刀”!跟在她后面上车的是一位衣着华丽的女人,夸张的香水味简直可以熏死蚊子。对比之下,很是讽刺,现实就是这么的血淋淋。许是那咄咄逼人的香水味的缘故,女人一上车,便引起了车厢内乘客们的侧目。她顶着“爆炸头”,鼻梁上的眼镜恨不得把整张脸都淹没。只听见她脚上的“恨天高”在车厢内“蹬蹬”地响着,显得格外刺耳。我不禁好奇起墨镜后的那张脸,那许是一个生活宽裕、趾高气扬的女人吧,抑或仅仅只是为了用夸张的打扮来掩饰内心的空虚。我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她于我而言只是个过客,而我于她只是个看客。
吸引我注意的是另一个女人,她静静地端坐在车厢的一角,她是那么的静,与车厢内闹哄哄的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她是什么时候上车的,还是一直就在那?我无从知晓,我仔细地打量着她,那一张不施粉黛的脸上没有过喜或过忧的神情,眼神是那么的清澈见底,她就那么静静地、淡淡地坐着。那许是一位教师吧,抑或是个学者吧,我竟从她的穿着和表情上看不出任何有关她职业或身份的痕迹。我正费力地想着,车厢内报站的广播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声音礼貌但却没有任何温度,如同身处的这座城市一样。
等我下车时已是黄昏了,天边的晚霞红彤彤的一片,像喝醉酒似的。“明天定然是个好天气”,我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