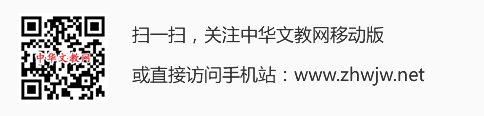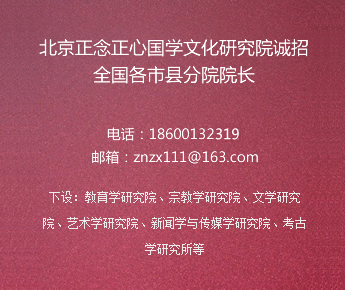——与著名诗人张庆和先生面对面聊诗歌
刘飞鹭
“见到你们就很高兴,你们是希望和未来呀!……上学的时候也有过文学梦,但在那个时代我丢失了这个梦,许久不再提及,也不敢想象。直到后来,遇见一个女子,她帮我找回来啦……!”
作家、诗人张庆和老师,初次和《当春》小记者们相见,便率真得可爱。写诗与爱情有关,谁说不是呢,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嘛。已经年过六旬的庆和老师,身材清瘦亦如他的诗歌,就连和小记者们的交谈都是心底可见,老者无谱,少者无拘,围着长桌便拉开了话匣子。
诗书万里送真情
张庆和:记得那是44年前的初夏,部队5年,我第一次休探亲假,路过北京在二哥家小住几日。傍晚,我正和哥、嫂在屋里聊天,家里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携着窗外一股洋槐花的香气进来了。姑娘与哥、嫂并不陌生,还没有落座便问“这是他五叔吧?”寒暄几句后,家里又来了客人,姑娘便到里屋和侄女说话去了。后来,我如期归队返回了青海高原,继续部队生活。
不曾想,这位初次谋面的姑娘,对庆和老师一见钟情,也正是这份感情唤回了他那丢失的文学梦。三个月后,他接到二哥的来信,提及那天晚上问“这是他五叔”的那个姑娘,并说双方的两位嫂子都想给他们说媒,问他意见如何?
正值青春年华,庆和老师岂能错过这样的美好:太好了,真是求之不得!赶紧写回信答复吧!
但那时他心中并不是自信的,且在信中如实相告:我在荒无人烟的高原,姑娘在繁华如涌的都市,这差别人家是否想过?
一个月后,二哥又来信,并附姑娘的通信地址,嘱咐说:一般都是男方要主动些,你们就处处看吧。
就这样,一场马拉松式的“写恋爱”经历就在他和那位姑娘之间展开了。
张庆和:随着时光的流逝,来来往往的信件如雪花纷至,越来越多,彼此爱意也越来越浓厚。信纸上的话语虽然已经将两颗年轻的心拉近,可又总也难以表达内心的思念和爱意,甚至有点隔靴挠痒、纸上谈兵的感觉了。那样的时刻,我们是多么渴望两个人能见上一面啊,就像如今网友为了见面翻山越海一般,但我们那个年代,连通一次电话的可能都没有。怎么办?现实中短缺的,就去向往的“情境”里寻找吧。
就这样,庆和老师的第一首爱情诗隆重诞生了。
新月弯弯
柳帘羞面
湖边,你手指绞弄柳叶
“我们……”
话刚露头
又被两片樱唇儿咬断
踏踏踏……
你甩下个背影
拉长我的视线
从此,你身上
就总缠着
用我的目光铸成的索链!
张庆和:无疑,这完全是“实境”里没有,却在“情境”驱使下营造出的一种“虚境”。但“实境”的确又是一种真实存在,正是因为从“实境”这个潜在的“有”出发,通过展开想象的翅膀,首先营造“虚境”,而后再穿越“虚境”这座桥梁,达到了内心的那种“情境”(也堪称花前月下吧)。后来我就把这首诗取名为《索链》。
这是诗歌的魅力,更是文学的魅力,语言不多,意境深远,意味深长。庆和老师把自己的情感落定在每一个文字上,想象着与姑娘相见。于是,我们在这首小诗中读到了作者内心炽热的情感。原来诗是可以这样写的,写诗是能够用来温暖生活、抚慰心灵、交流情感的。那样的日子,思念是一条河,继而他又写出了《没有你的日子》《苦涩人的歌》《就因为有那样一种心情》《月圆的时候》《我身旁流着一条小溪》……在爱情的河岸,庆和老师为她心爱的姑娘留下了一首首长长短短的诗歌。

《当春》:这么多年坚持创作,您认为诗歌和散文有什么不一样?您一直坚持创作,心里所秉承的信念是什么?您能讲一讲诗歌的创作技巧和方法吗?
张庆和:诗,是文学的最早和最高形式。对此,似乎已经没有了争议。诗,是多元的复合体,企图用一两句话、一两篇文章去解释它,那是天真和幼稚;企图以庸俗、简单的方式去对待它,更是对诗的一种亵渎。
分行排列的文字不等于诗,名词概念的堆砌不等于诗,无病呻吟的“哇哇啊啊”依然不等于诗。诗言志,但这并非要人去图解政治,移植口号,照搬生活,说教人生;诗言情,但也并非要人扯破嗓子去喊虚虚飘飘的豪言壮语,抑或洒几粒哭哭啼啼的缠绵泪滴。
诗,毕竟不是散文,不是小说,更不同于新闻报道。诗就是诗,它需要凝炼,因凝炼而需要含蓄(并非晦涩)。为人贵直,为文贵曲。古人论诗曰:“直说易尽,婉道无穷。”含蓄是诗特有的艺术手法,含蓄是待放的花蕾,可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可留下空白供人想象。因为,任何一件成功的作品都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创作完成的。
作为文学最高形式的诗,就其表现手法而言,不只是要凝炼、含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构思,比如角度,比如形象思维,比如意象空间的营造……同时诗也需要包装——需要语言的美。因此,锤炼诗句也是为诗之道。很难设想,一个连语言都没能过关的人,会写出什么像样的诗来。
诗一旦发表,就属于社会,切莫把它当成私产儿戏之。因此,用分行体“言志”或“言情”的诗人和写诗的人们,理应经常拍拍脑门,想想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已经出世或即将出世的“宝宝”。
诗,不仅仅是悬挂在人类脸颊的一颗泪珠;诗,不仅仅是建筑在心灵深处的一间小屋……
生活是基石,情志是灵魂
说起写诗技巧,庆和老师坦率回答:“还真的说不出,有很多写法也只不过是经过了多读、多察、多思、多写,加之经验的积累和领悟、熟能生巧而已。至于诀窍、技巧之类说法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但生活是基石,情志是灵魂,想象是翅膀,这些重要元素还是离不开的。”
张庆和以自己和妻子九年的牛郎织女生活为源泉,以一首首情诗为例,将生活、情感、想象等多重元素加以创作,收获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张庆和:在结婚分居近十年之后,我和爱人终于团聚。《夏日小河边》,正是那一刻所得,也是我比较中意,并引起朋友们关注的一首精短小诗。那是一个温馨的周日,雨后天气晴和,我和妻子骑车来到郊外。拂柳斜阳,涟漪波光;头顶的蝉声,脚下的碧草,还有那条弯曲着伸向远方的小路以及路旁娇俏的野花……此时此境悠闲自得,处处铺满诗意。
柳荫锯碎阳光
粉末满河道飘荡
诱惑在前方悄悄拐弯
蝉声兴冲冲织网
碧草欲挽留脚步
不小心惊动了芬芳
张庆和:这时期,我已经能够自觉调动起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通感融入诗歌创作、表达情志,进而让诗歌更加凝练和耐咀嚼、有味道。
又如还有《那一场雨》,庆和老师说,从字面看这首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好像就是在写一场旱天逢甘霖的好雨。其实,写这首诗时有个背景,就是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心感触很多,不由得文字从心中涌出。
风儿似温柔的手
轻抚云的秀发
云感动了
喜悦的泪滴滴答答
一场等待许久的雨
在期盼的日子里飘洒
直惹得无数春光
一阵嘁嘁喳喳——
是时候了
快醒醒吧
该发芽的发芽
想开花的开花
要追梦就甩开矫健的步伐
于是
一粒种子又一粒种子
悄悄出发
一片叶子又一片叶子
一天天长大
一只蜜蜂又一只蜜蜂
忘记了回家。
张庆和:《讲话》实在朴素,毫无官腔衙气,讲在理上,说在根上,内涵十分丰富。
习总书记还坦诚地告诉大家,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而且还很高兴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贾大山就是他十分喜欢和尊重的作家,以致两人成为好朋友。这说明,领袖和普通人一样,都有着共同的人间情感和心理需求,大家的心是相通的——老百姓喜欢的作品领袖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赝品,领袖也同样厌恶。
那些在文艺作品中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的垃圾作品,大家早就有目共睹,愤而指之。好风携着润雨来,激浊扬清正当时。这就是写作《那一场雨》的心念。
生命中,那一枚文学的种子
庆和老师出生的年代和家庭,留给他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贫穷。但令他最为骄傲的是有一个乡村秀才爷爷。他在家中是老小,上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哥哥,因为农村的子女排行时,女孩子是不能算在内的,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小五”。便是前文中的“这是他五叔”了。
庆和老师三岁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病倒后不幸离世。他是在奶奶和大姐的疼爱下长大的。爷爷是村子里的一名教书匠,因是读书人,自是爱书如命,屋子里有几大箱子的古书。爷爷一肚子的故事,都是从那些书上来的,比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三国志》,还有一些宫廷传奇等等。
他印象中的爷爷像个说书先生,时常会在村子里为大人和孩子们讲上一段历史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村子里的大人孩子们自然也都爱听。有时家里来了客人,也会邀请爷爷讲上一段,而庆和老师则是爷爷最虔诚的听众。那些天南地北的事儿,和故事中性格鲜明的人物不知不觉间在他的心里也扎下了根,令贫穷清苦的生活多了几许趣味。
爷爷的书虽然古奥难懂,却拦不住小孩子的一颗好奇之心。年少的张庆和常常翻看爷爷的书,上小学三年级时就捧着《三国志》来读。虽然有太多不认识的字,也读不通语义,到底是囫囵吞枣地浏览了一遍,故事明白个大概,这也足够一个小孩子自豪一番了。
除了对诗歌情有独钟外,他更喜爱散文。他记起了自己在小学三年级时,第一次学写作文《我的家乡》。一口气写了一千多字,家乡的山山水水、野趣巧遇由笔端泉水般汨汨涌出,尽管有太多的字不会写,作文本上标着多多少少的汉语拼音。他未曾想,这篇自以为十分稚嫩、平淡的作文,竟然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评价,并在全班作为范文朗读。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任何一种鼓励和赞扬,都有可能成就他不大不小的梦想。爷爷为他种下了一枚文学的种子,老师又为这枚种子灌输了营养。此后每当他的作文在自己的班级、其他班级,甚至高年级中去朗读、评析时,那枚种子如同得到了阳光雨露般生长着。
正当庆和老师雄心勃勃,立志在文学上要有一番作为之时,学校停课,图书被烧,知识的尊严荡然无存。那是一段伤痛的历史,经历了自然不会忘记。他在后来的作品中所述:“愚昧和无知扬起的漫天尘沙迷蒙了我的双眼。从此,我不再读‘闲书’,不再‘胡思乱想’,与‘有所作为’彻底决裂,这一绝就是十四年。这十四年,正是我生命蓬勃、获取知识的美好年华啊!可惜,我失去了,永远地失去了!”
作品中的思与想
读庆和老师的散文和诗歌,你不能不关注读者对他作品的评价。这里引用两段评论者的话:“张庆和是散文家,我读过他的散文集《哄哄自己》《心灵呓语》。当时总的感觉是这位作家内心世界广阔、精神生活丰富,敏锐的思想和艺术想象力支撑着他的创作主体,并得以充分的诗意抒发。如果简要地概括庆和以前的创作主题,我以为是发现美表现美。尽管美不只属于创作主体,也不只属于创作客体,但对庆和而言,他首先具有能感与易感真善美的执著的创作主体,否则,他不可能坚持这个主题到如今。
“美在心中是爱。庆和的诗文进行着爱的传递,读它们如同走进充满爱的温暖殿堂,用爱拥抱生活中的真善美。在当今所谓‘情感危机’的现实生活中,正是庆和这一创作个性的彰显,他才有那么多的语言美、文学美、人文美、精神美的诗文被选入初、高中语文教材,才有多篇名篇散文被选为中考语文试题,才有那么多作品获奖,或者被译到国外。庆和的诗文是‘情感教育’的好教材。”(见孙武臣:《创作主体的诗意抒发》)
在小记者们提到散文《坝上月》,向他寻求创作的背景和思路,他便讲述了与友人,在坝上的相遇,并以明月为元素抒情言志。他说:“月亮如饵,诱惑了千般心情;月光如丝,柔柔地织成了一张巨网。我的心被这网捕捞住了,情便无处逃脱,任由这网的摆布……”
“我相信月,相信这坝上的月;我寄希望于月,寄希望于这坝上的月。我将走向一片莹洁与美好。因为,这坝上月已经高高地悬挂在我心的天空,永不陨落……”
“千古明月别样情。”于是又有评论这样说:“月还是那轮月。古往今来的大诗人大文豪不知为之吟咏为之歌唱为之迷醉了多少次的明月。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人们身上都有不同的诠释,张庆和就是勇敢地跳出前人的一位赏月者。他没有沿袭常人笔下花前月下的缠绵,也没有承袭古人疯子般豪言壮语、对月狂歌狂饮的骄躁,而是以一种沉静、平常和超脱的心境来读月的!《坝上月》这篇散文可谓是视角独特、意境丰满、文思绮丽、笔触深沉而凝练、构思别出心裁的佳作。”(见秦人:《千古明月别样情》)

“张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散文《峭壁上那棵酸枣树》,您能谈谈这篇文章中的构思吗?”
看着小记者求知若渴的目光,庆和老师笑了:“优美的文章源之于优美的构思,构思的优美决定了文章的优美。或许是身居其境,美从中来,你感受到了,接收到了周遭的一切。而这一切是信息,一棵树,一枚叶,一片石,它引你思考,也引你入境,你的思考肯定离不开现实,因此你作品的深度自然也是你思索的深度。毋庸置疑,作家,作品,首先是个性,其次是社会性。因此,也可以说构思层面决定着作品深度。”
作家张文睿先生这样说:“在庆和老师的诸多诗作中,有两类作品值得研究探讨,值得较大范围的传播。一类是庆和老师写的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的重大题材与主旋律诗作。这种思维方式,需要高度的政治修养,历史修养,还有哲学修养的支撑。同时,庆和老师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其特点是,口语化入诗与从容平静的叙述,从而达到了浅草下有深泉的境界;庆和老师另一类值得研究探讨、值得较大范围传播的作品,是他的短诗,看似细碎,却有珍珠般的品质。”
与庆和老师短暂的交流,他的语言,他的黑白文字,深情无邪,实为诗人品质。天赋固然重要,然靠近庆和老师,他的真诚与勤奋最是我们写作的旁样。
张庆和简介:共和国同龄人,原籍山东肥城,定居北京,部队转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一级作家。有多件作品被文摘类报刊转载、获奖,并入选数百种图书,或被译成英、法文字出版发行国外。另有《峭壁上那棵酸枣树》《海边,望着浪花》《起点》《面对草地》《坝上月》《哄哄自己》《问候心情》《关于“水的职称”说明书》《仰望雪山》《我是雨滴》《海滩上,熟睡着一只海螺》等数十件诗文作品分别入选初中、高中学生升学“语文试卷”、毕业质检试题、模拟试卷或中小学生“语文阅读”教材等。已出版诗集、散文集《山野风》《美丽的梦》《颠簸红尘》《写作没有技巧》《娃娃成长歌谣》《灵笛》《哄哄自己》等十余部著作。曾出席中国作家第五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其辞条入选《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
作家的魅力是感染阅读者
在《当春》编辑部的组织下我们见到了著名作家、诗人张庆和老师。张老师是一位朴素的长者,带着微笑与我们侃侃而谈。首先我们都各自做了简短的介绍,交谈了对诗歌的认识和写作的动因,这些小的问题,也成为张老师那个时代的一点禁忌,不可以随意的吐露。
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有一定的原因,而张老师的写作是因为与恋人的通信,再到用诗歌来传递爱,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也是不能取代的方式。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时代中,文学精神都需要一种文化的激励与传承,诗歌是最好的载体。
而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时常会在想,我们写的文章其他人看得懂吗?
张老师对于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讲解。我们写作主要是抒发和我们有关的,对于周围事物的反馈,才会形成思维上的跳跃。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思维逻辑和语言,再到写成诗歌的过程,应该是以自身喜闻乐见的,或者悲痛的感受为元素。所以就会有一些或者一群与你一样的思维者,这就形成了群体性。当然有些负面的思想我们应该正确认识,才能起到好的引导性。
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诗歌的载体与散文有区别,所以在理解上我们就不能靠单一的思想去认识。我们在写诗的时候,应该符合自身和周围的事物,去感染阅读者,这个阅读者可以是你爱的人或者是群体性的。这就要求我们多读与多写,才能达到对于诗歌主题的控制。
诗歌的争议性,有一些老师认为分行排布不押韵就不是诗歌,张老师也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
诗发展到现如今形成各种流派,以及各种争议,这对学生时代的我们应该用我们认为的观点去看待和证实,才能看到什么适合我们,便于展现思想储备。
——顺义九中 王一凡
参加了编辑部组织的“作家面对面”,与著名作家、诗人张庆和老师的交流活动。张庆和老师在生活中对我来说不是很陌生,我大概知道他写的一些文章,还知道他写的作品曾经多次发表于全国各类报刊杂志。通过这次和张庆和老师的交流,让我懂得了文学是非常有魅力的。
张庆和老师给我们讲了他的几篇作品,其种《峭壁上那棵酸枣树》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这是张老师因为要参加一次征文,创作后多次修改都不尽如人意之后,又写了另一篇文章来释放内心的压抑所创作出的作品,以此来阐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张老师能够成为著名的作家,创作出如此多优秀的作品,缘于他前期牢固的诗歌基础。当我提出怎样才能够多一些写作的灵感时,张老师给我们提出了几个词语:“多读(丰富的知识储备),多看(开阔的生活视野),多思(开采心灵深处的矿藏),多写(打牢走向文学高处的基础)。”喜欢读的文章一定要多读,好文章一定要看得非常细致,只要对阅读的文章多一些思考,那么自己在写作时,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有深度。
张老师还重点说到:“写文章一定要以练笔为主,不要急于求成,只要慢慢来,一步步走好每一步,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顺义九中 闫子龙
转自《校园文学·当春》2017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