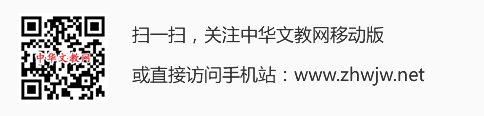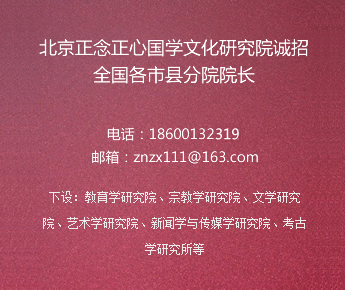(王贤根左,童村右)
我对作家王贤根先生的称呼有点儿复杂。
一般情况下,我都称他为老兄或者老哥;公开场合里,我则统称他为王老师。而在有些特别的时候,我还会热贴贴地叫他一声根哥。其实,对他怎样称呼,是完全由着自己的心情的。从严格意义上说,王贤根先生是我的师兄,当年读军艺文学系,他是二届的学员,而我则是六届的学生。照这样说来,对他冠之以师兄的称呼,或许更恰如其分一些,起码听上去,有一种同根同源的感觉,就像一家人似的。
不妨就这样复杂地称呼着。
众所周知的是,王贤根先生是一名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他的《援越抗美实录》《中国秘密大发兵》《西线之战》《西部之光》《火红的太阳》《邓东哲将军纪事》《雷神》《远泉绿色之梦》等,相信很多读者都已拜读过。我一向认为,如果你真心想认识一名作家的话,那么最直接也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去一一解读他的作品。所谓文如其人,也许正是这个道理。
算起来,我与王贤根先生认识应该有很多年了。先生生得精干,长得少面,俨然是典型的江南才俊,加之他重感情,人缘好,他的身边自然是少不得许多文友相随的。约略记得,最初与他相识,是在一个文友热心张罗的一次聚会上。那次聚会极是热闹,一大桌子人你一言我一语,始终被一种高涨的情绪包围着,气氛由此显得煞是活跃。先生的话不多,又很少插话,只是坐在那里静静的听,脸上却保持着一种矜持的微笑。尽管那次聚会,彼此之间都一一经主人事先进行了介绍,相互之间也十分热情地握过了手,并留下了联络方式,嘴里说着以后不要断了联系,但事过之后,我与他之间却并不曾有过直接的往来。
真正接触和了解王贤根先生,是在两年前海淀区作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有一些重要的决议要产生,所以那次会议开得有些漫长。等到会议结束时,已是半下午的时候。离开会议室时,不知因为啥儿,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远处走一走,便向走在身旁的他随兴问了句什么,没想到他十分爽快,一口答应愿意陪我同往。接着,他便又约了另一位好友,驱车直奔西山而去。
那一次我们去的地方是门头沟的马致远故居。
事到至今,我仍是想不清楚,当时为什么就去了那么一个地方。说起来,很有些鬼使神差的意味。
这个被当地村民世代传说的马致远故居,坐落在门头沟区王平镇韭园村的西落坡村里。那是一个十分古朴而别致的村子。院门前驻足四望,远山近树尽收眼底,脚下边站着的,则是一拱小小的石桥,石桥下流水潺潺,让人不由想到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故居的院落不大,却设有书房、卧室、客厅、厨房,院落的一角还筑有一间马厩。
大概是由于长久没人居住的原因,到这时,整个院落已经显得十分破旧,院内的石缝里,竟自由疯乱地生出一丛一簇的野草来。触景生情,眼前的这番景象,不能不由人心怀忧伤。
王贤根先生看得仔细,一处一处地在故居里走过,于桩桩件件的旧物前,徘徊复徘徊,或抬手轻抚,或沉吟低叹,全然一副不茍言笑的认真样子,脸上的表情也甚是凝重。此时此刻,我想,他的想像已经长了翅膀,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是不知道的。然而,从他的步态与表情里,我却一下觉察到了作为一名称职的作家令人感佩的悲悯情怀。
“西村日长人事少,一个新蝉噪。恰待葵花开,又早蜂儿闹,高枕上梦随蝶去了。”走出了马致远故居,王贤根先生有些感慨地说道,“马致远在《清江引·野兴》里所说的这个西村,理应就是这西落坡村了。”
稍倾,他又说:“从古至今,许多胸怀抱负的文士,都是在官场上不如意的。由此远离权贵,退隐山野,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而马致远之所以决心离开繁华热闹的戏剧舞台,独独隐居在这偏远的小山村里,也许是自有他的道理的。”
我咀嚼着他这番话,点头应诺道:“只是不知,这落坡村的名字,当初是谁取下的,那么让人感伤。落坡落坡,走到这一步,他也确实陷到了一个落魄的境地了。”
王贤根先生笑笑,说,“酒中仙、尘外客、林中友、曲中游,又何尝不是一种好生活呢?”
驱车回程的路上,不知怎么,他竟然一下子沉默下来,就像是怀揣了满腹的心事……
就是从那次之后,我们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稍稍的日子长了,彼此间便有了牵挂,或发个短信,或打个电话地问候一下,哪怕是三言两语,也成了一种慰藉。
王根贤先生把那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千古长城义乌兵》赠送给我的时候,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请雅正。他笑着说。
他在那部书的扉页上,也是这样写的,字很漂亮,有些赏心悦目。
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话一向很少,脸上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而少有愁眉不展的时候。
那部厚厚的近三十万字的纪实文学,我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终于把它读完。末了,竟有一种余兴未尽、欲罢不能的感受,心里头却又是沉甸甸的,如同压了一座山样。
这些年里,我读书很少,即便是读了,也大多是那些国外作家的作品,而对国内作家特别是当代作家的一些所谓的精品力作,关注的力度实在让自己深感惭愧。也许正因为此,所以当我拿起这部《千古长城义乌兵》的时候,一字一句读下去,满心里充满的是由衷的钦佩与敬畏。
我知道,王贤根先生为了写这部书,前前后后整整耗去了好几年的时间。曾三次自费到长城沿线采访,三次赴义乌与市志编辑部同仁交流。收集、查阅、寻访,求证,对于那段过往的历史,几乎严谨到了近于苛刻的地步。一字一句煎心熬血最终落在纸上的那些文字,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境界。
如实说,在读王贤根先生的这部《千古长城义乌兵》时,我的心里是始终有一种痛的。整部书中所弥漫着的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不由间令我一次一次掩卷遐思,心潮起伏中,顿然间就会泪眼模糊。
书中描写的是,四百多年前,大明将领戚继光,在平息了多年为虐的东海倭患之后,毅然率领几千近万名浩浩荡荡的南军北上,千里迢迢固守边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是怎样一砖一石构筑长城,又是怎样在一个个漆黑而又漫长的夜晚,忍受着难耐的寂寞,一边用一腔热血抵御外侵之敌,一边用百般柔肠怀想家中的妻儿老小的。
四百余年的凄风苦雨里,那些像种子一样洒落在长城脚下的义乌兵卒,在远别故土的那些岁月里,内心深处应该有着怎样绵延不绝的乡愁呢!
血与火,情与义,跃然纸上。在近三十万字的浩繁文字里,我就这样追随着戚家军铿锵作响的脚步,一步一步在历史的罅隙里穿行,风雨无阻。
因为乡愁,所以寻找。于是也便有了一个个泣血带泪的鲜活人物。
因为乡愁,所以回归。于是也便有了一桩桩动人心魄的情感故事。
忧伤,但是美好。这应该算是我对于这部作品的初步印象了。王贤根先生之所以也很看重这部作品,我想,这是很有他的根据和道理的。
我在想,在写这部书时,他的内心一定是丰盈而孤独的。有这样一种创作心态的作家,必定是值得尊重与敬佩的。
说起来,我与王贤根先生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这年的初秋时节,这个时候,夏日的暑热尚未完全褪去,我与他一起,有幸参加了海淀文联组织的一次艺术家赴湘采风活动。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同住一舍,相谈甚欢,那些谈话的内容,又大多都是围绕着文学展开的。说到当前的阶层化与关系化写作,以及种种不尽人意的文坛怪状,两个人免不了要唏嘘上好一阵子;而在说到各自将来的创作打算时,他不免又对我好一番勉励。
他很真诚地望着我,说:“你好好写,实在不行,到时我带你去敲他们的门。”
他所说的,自然是出版社的大门。
这句话让我很受感动。有了这颗定心丸,我想,我是不应该辜负了他的。
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采风团走过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因为有了他,整个团的气氛由此也变得活跃起来。尽管他仍是很少说话,然而一旦开口,常常又是语惊四座,风趣幽默得让人忍俊不禁,由此,有他的地方,自然又是少不得欢声笑语的。一个时时刻刻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有谁不愿意与他共处呢?
印象深刻的是,那几天里,采风团的十几个人,是爬过了两座山的。我自小是在平原上长大的,不知因为什么,每当见到了大山时,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因此,无论山大山小,我常常坚持不到山顶,便有些泄气地在半山腰处驻足不前了,但是,王贤根先生却不然,看上去,他虽已是花甲之龄,却似乎对每一座大山都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走在山路上的样子,恰如闲庭信步、如履平地一般。若是遇到稍稍平缓的地方,他竟然还能一路小跑,将左右人等远远地甩在后面。
我知道,他是在南方的大山里长大的。对于他来讲,走进大山,自然就像走进了故乡一般了。
后来的一些日子里,自觉与不自觉间,我常常就会想起他上山走路时的样子。而每当想起这一幕时,无形之中我总是会产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昂扬向上的力量。
( 作者童村为北京市海淀区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