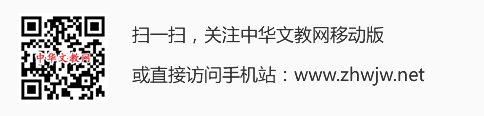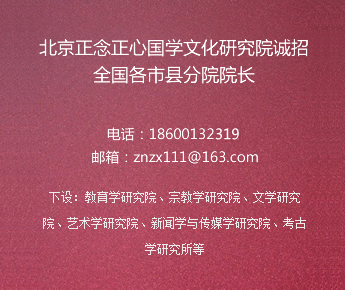作者:姚雪
我对地坛的记忆,是在儿时第一次的庙会。在我的记忆里那里永远是人山人海,热热闹闹把冬日的寒冷蒸腾出了去。与父母一起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是多么的快乐,从不是我想的问题。我只负责用那童心去看成人的世界。也从没有考虑过以后怎样去活?
当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被告知我不会再回到我的家乡去上学了,我只是默默地承认。不去抗拒它因为那没用。我接受了眼前的一切,陌生的一切,包括语言,包括生活。
小学来了,初中来了,紧接着就是高中。
“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我的心魂是什么呢?恐怕我自己永远不能给出这个答案。可能会由我未来的伴侣来揭开吧,她会带来正确的答案。
有些东西确实是任谁也不能改变的。落日就在那里,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把无限的景色收揽在了人间。
心,就在这里。就在天地间。任谁也无法改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
良久无言。无论我做了什么。她会说我是她的骄傲。我是她的骄傲......
“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说对了。
那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
什么才是灾难,是自己被打倒后还没有勇气站起。
“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它们是相连的,罪恶和福祉。那何必悲伤呢。
再过十年,也许社会终于将我同化。一个西服笔挺的满身铜臭的人,在不知为何而奔波,靠着酒精而麻醉。
“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这里,心,是任何都不能改变的。
(作者地址:南京农业大学(经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