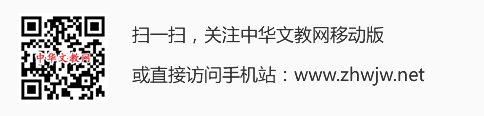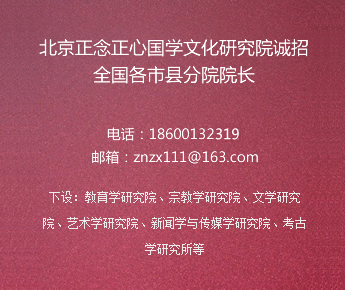读写障碍成被忽视的“魔障”
被忽视的魔障
站在同样的跑道前,别的孩子是速度赛,读写障碍儿童却是跨栏赛——很多时候,这些障碍甚至不被旁人认知
7岁的男孩文文,面向镜头,讲述他最大的心愿:“如果我有原子弹,就把学校给炸了。”他的神情没有变化,就像说“如果我有五毛钱就要去买口香糖”一样自然。
文文讨厌学校,讨厌学习。他读课文,一个字念完了,可能要看上两秒钟才蹦出下一个词。他写字,总是写不进田字格里,一笔一划戳在纸上,“就像刨地似的”,他的老师说。
文文是一名读写障碍儿童,也是老师们眼中的“差孩子”。
在中国,像文文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站在同样的跑道前,别的孩子是速度赛,他们却是跨栏赛——很多时候,这些障碍甚至不被周围认知。
根据国际读写障碍协会(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的界定,读写障碍是一种学习障碍,特征是不能正确发出或接收口头或书面的语文信息。读写障碍儿童在拼写、组词、阅读、书写等方面都会遇到困难。读写障碍是特殊学习障碍(包括读写障碍、特殊语言障碍和操作协调障碍等等)中最常见的一种。
跳字漏行、增字、替换字、倒反念、混淆相似字、写同音异字、镜反字、字体歪斜大小不一、英文连字不空格、看不懂数学应用题、无法理解阅读内容……读写障碍的常见特征虽多,却很少会同时全部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成长的痛苦
读写障碍人群究竟有多大?来自美国全国保健研究所2004年的预计,美国约有15%人口受到各类学习障碍所影响,其中已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当中,有8成以上属于读写障碍。
曾经有人认为,英文是表音文字,字母的不同顺序影响读音;而汉字是表意文字,像图画一样的外形与读音无关,因而中国儿童应该没有读写障碍问题。然而早在十多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翔平便发现有读写障碍症状的中国孩子。
事实上,汉语的读写障碍更加复杂。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而读写障碍的孩子形音捆绑加工能力落后,即便好不容易捆绑上了,转录的速度又比别人慢几毫秒”,刘翔平教授解释他的研究成果。
有香港学者调查指出,香港儿童存在读写困难的普遍率高达9.7%至12.6%。而在中国大陆,对读写障碍的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进行过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只在部分地区有零星结论。
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两位教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市某城区4所普通小学3至5年级平均年龄为9.41岁的1200名学生,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诊断第10版中阅读障碍的定义,采用逐层筛选的方法诊断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结果显示:阅读障碍的发生率为6.3%。
“5%~10%,是国内被普遍接受的读写障碍儿童比例。”刘翔平教授说。
他接触到的读写障碍儿童,“普遍低自尊、学习动机低下。像奴隶似的,没有学习的乐趣和投入”。
另外,“相当一部分读写障碍的孩子,注意力也存在障碍,两者有重合部分”。
还有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某学习潜能开发中心的创办人兰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接受矫治的300多名孩子中,有40多人同时还在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过分敏感、强迫症、习得性无助,还有孩子出现自杀倾向。
“读写障碍不是病,不可能药到病除,这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过程。改变和接纳是平衡的,一边接纳它,一边改正它”,刘翔平教授深感中国家长的急功近利,“事实上,阅读是勤能补拙的,虽然不能治愈,但可以补偿。一旦孩子认识到两三千字,这个瓶颈效应该可以过去。这需要家长花力气花时间来抓一抓,将阅读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家长们总是希望走捷径,恨不得找到‘神医’让孩子改头换面。”
在独生子女政策与激烈生存竞争的当代中国背景下,这样的焦灼尽管可以理解,但在另一方面,家长和孩子其实可以不被分数所困。人们常举例3岁才会说话的爱因斯坦、反着书写的达·芬奇、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读写障碍者并非意味“懒惰、弱智”,相反,他们在音乐、绘画、运动、设计、电子、机械、戏剧等领域可能有着超出常人的禀赋。
于是,在国外,阅读障碍者被俗称为“聪明的笨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威曾参加一个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学习障碍研讨会。3000多人的会场,除了专家学者,一大半都是家长。一些八九岁的小男孩盘腿坐在主席台前的地板上听,听完后上台演讲:“我有拼读障碍,但这并不妨碍我学习……”
这让梁威印象深刻,“这样的场景,你在国内绝对看不到。”
忽视与进步
中国读写障碍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陆较香港台湾地区为晚。在此之前,从19世纪中叶起的临床医学报告个案、20世纪提出学习障碍概念、直至上世纪70年代教育立法,西方的学习障碍研究已走过漫长路程。
1949年,国际读写障碍协会成立。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成立了读写障碍研究协会。2000年,梁威教授等人参与成立了学习障碍研究专业委员会,挂靠在中国教育学会儿童心理专业委员会之下,是一个三级学会。之后,随着国家对三级学会的管理调整,这个委员会自动解散。目前的研究,多以课题形式存在。
至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诊断评估标准可以用于汉语阅读障碍。有的学者用识字量,有的学者用阅读测验判断是否低于同年级水平,还有学者翻译修改国外学习障碍筛查量表。而提供读写障碍矫治服务的教育机构,国内知名的不过三四家,矫治理念也各有不同。从基础到应用,读写障碍研究在我国仍在“初级阶段”。
“在大陆,教育心理学讲的是普通人,特殊教育又在讲残障人士。而这一大部分读写障碍的,无形中就成了(谁也不管的)边缘人物。”刘翔平教授说。
而在台湾,《特殊教育法》将学习障碍与智能障碍、视听觉障碍并列,共同称为“身心障碍”列入保护。2010年6月,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发布了一份《为学障学生提供服务》的文件,明确表示,“经评估确定有读写障碍的考生……可提供适当的特别考试安排”。
这些安排可能包括:笔试时间延长四分之一;考生可以隔行或者隔页书写;90分钟或以上的考试,考生可申请每45分钟休息5分钟。另外,考评局还可以为学生印制单面试卷,甚至提供象牙色的卷子。
香港的小学还会对刚入学的孩子进行早期识别。如果在指定机构测评为读写障碍,孩子们将获得香港教育统筹局划拨给学校的特殊教育基金,每位孩子1万港元。美英等西方国家也有类似政策。
“其实,这些政策是在减少未来的社会投入。”刘翔平教授说。旅行时,他曾注意到邻座的一个姑娘。一份报纸,她读了四个小时还没有读完。细细一问,她是化妆品销售员,没有上过大学。
有数据显示,只有大约8%的读写障碍者可以完成大学学业。而染上网瘾、酗酒,或是失业乃至犯罪,被应试教育淘汰的另一部分,有可能成长为社会的不安定因子。
刘翔平教授、梁威教授和兰紫都努力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讲座推广这一理念。然而,在一次会上有家长听了兰紫对矫治读写障碍的介绍后,回家一问,身边没人听得明白这件事:“其他人都不知道,你肯定是骗我的!”
那位在她面前说心愿是“用原子弹炸学校”的男孩文文,最终也没有来接受矫治。文文的妈妈回家后向老公提起,不料老公责骂她:“你才脑子有病!我的儿子没有问题!”奶奶也不赞成:“花这钱,还不如请个家教让他好好学习呢。”
兰紫深感常识普及还要继续,因为,“只有公众的了解,才能最终产生对这个群体的理解”。 记者/陈薇 文/ 王一凡